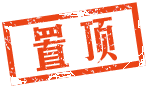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特仑苏羊奶 于 2023-11-7 14:44 编辑
到了那儿之后,目及四周,满眼皆是及膝的无人修剪的软硬杂草,并且旁边还有一个超大的垃圾坑,不知道是人造的还是后天天然形成,里面充斥着各种颜色不一的塑料袋子和破碎的玻璃茬子以及当下站在高处不能单凭肉眼分辨出来的杂物,尤其当属塑料袋子占据多数。工厂的外侧,斑驳不堪的墙面好像随时都在剥落附着在墙体上不太牢固的碎石片。看到这个满目苍夷差不多令人遗忘年久失修的地方后,我们竟然都不约而同地表示出相当满意。这就好比一个跛子或者一个瞎子总之身体某一部位有些残缺的男子在面对一个长得不是那么水灵漂亮的姑娘在考虑实际问题后便不会逐一挑剔进而欣然接受。
走近之后,工厂内的各种嘈杂喧闹声顺着虚掩着的破铁门扑面而来。看来有人比我们捷足先登,而且还是不少人。也难怪,不出方圆十里,就这么独数一块儿的风水宝地,咱们注意到了,别人肯定也会嗅着味儿前来分一杯羹。
跨进去之后,嗬,热闹非凡,仿佛这是一座为了躲避朝廷追查迫不得已而隐匿大漠之中的龙门客栈。
我们的到来使这种喧闹暂停了一下,倏的安静下来。仿佛身穿制服的警察忽然闯入经营不良的夜总会,让人有着猝不及防的错愕来不及防范。或许是看到我们一帮人不像是实地考察拆迁废旧工厂的工作人员,便又转过身去继续各自的游戏,接着恢复了中断片刻的喧闹。
环顾四周,似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我们休息消遣的空地。好在是我们的人数不算多,和其他“团伙”协商好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之后,便算是在这儿扎下了根儿。
第二章 铁木真
结识钱青峰、张国强他们几个是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
那年,我爸和我妈把房子从旁邻的村子里搬迁到相隔数条蜿蜒曲折的土石子路和一条柏油马路的城郊的一处楼群,房屋的面积也从原来的五六十平米增涨到百十来平米,建屋的材料也从原来的黄砖青瓦变成了如今的钢筋混凝土。随之而改变的是我的眼界,也从原本的隔着庄稼地里一人多高的向日葵看日升日落变成了后来的驻足在客厅隔着不太密集的楼群观潮起潮落。
我很快又结识了一群新的玩伴儿和伙计。
我爸说的没错,“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可惜由于当年出于我对这句话认识的不足,所以所结识的清一色全都是“带把儿”的。唐晓菲是后来加入我们的,前后差不过一年的天气。她是我们这群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女娃子。当时我们乳臭未干情窦尚未初开,只能通过撒尿的姿势和去厕所的方向加以甄别。
第二天张国强发现了唐晓菲这个问题,于是他强烈建议就以“唐晓菲能否融入我们的队伍”召开一次会议。我们只好在用楼层隔板隔挡住暴晒的烈日的阴影三角区域郑重地召开了第一次“军事会议”。张国强觉得,自己提倡召开的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当年红军长征期间的遵义会议,起着拨乱反正之功效,弄不好最后自己还会像毛主席一样高屋建瓴地完成对当前整体恶劣形势趋势的果敢决策从而确立他在团体中英明的领导地位。
我说:“人是我带来的,她以后跟我。”
张国强说:“我们要排除异类,她跟我们不上同一个厕所。”
我据理力争说:“上厕所的都是我们的同志,管她上哪个厕所。”
后来我和张国强吵了起来,接着互相推搡着抱着对方摔起了跤,其他的一群白胖小子在周围围成一圈起哄煽风点火。我从他们不停跳跃间的缝隙中隐约看到唐晓菲杵在不远处的水泥台阶上手肘不停地抹着眼睛哭了起来,柔软的白嫩小手不停地揩着眼眶溢出来的泪儿。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唐晓菲的无助和哭泣给我带来很大的力量,就像液化气罐子上的黄色转扭接着扭了半圈火力加大,又像大力水手吃了菠菜。我们扭打着抱着对方的身体滚到阴影区域外,又接着滚回阴影区域内。强烈的太阳光铺满尘土飞扬的水泥地的同时也铺满了我们的身体,荡起来的灰尘在强光的照射下变得纤细而漫不经心。最后我把张国强打趴在地上,伙计们把筋疲力尽的我俩拉起来。就这样,唐晓菲融入到了我们的队伍。
很多年之后,有一次张国强找我喝完酒,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醉醺醺地说:“我记着你丫的还为了唐晓菲跟我打了一架,不过想着我们这群发小能出一对儿竹马青梅也值了。”
我呷了一口酒笑着说:“老实说,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想把唐晓菲发展成老婆来着,可思来想去就变了味儿。你想想,打小看到大,从你拿袖口儿揩鼻涕到你西服革履,要跟她在一块儿啊,总感觉缺点儿什么。知根知底,没劲。”
“是不是缺少了那种——陌生的刺激感?”张国强狡黠一笑。
“对对,就是这感觉。哎,我怎么发现你打小就有这种窥探人心的本事啊?”
当时我们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交接地带,似乎拥有相比之前更加广阔的天地。
每年仲夏,很多村子里的瓜地都要被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组成的“团伙”洗劫一番。仲夏处在孟夏和季夏的当间,很是炎热干燥。
刺眼的阳光透过杨树和柳树嫩嫩的叶子之间的缝隙,在土坡子上筛漏下斑斑点点的不规则的点点亮光。偶尔掠过一阵热风,懒懒地吹动杨柳树上枝条上的叶子,仿佛在试图摇醒趴在树上永不鸣叫的雌蝉。我正和一帮与我年龄相仿的半大小子趴在土坡子上准备策划偷相隔不远处李大爷菜园子里甜色沁人的香瓜。由于土坡子和菜园子相距不远,一阵一阵的熟透了的诱人瓜味儿随着热浪扑鼻而来。
林小枫把他的很多宝贝都装进一只布袋子提了一兜子,鼓鼓囊囊,走过来的时候一颠一颠的。仿佛早些年间黑白的抗战电影中裹着一头白毛巾的大婶胳膊上挽着一只装衣服或是热馒头的白布袋子。他找了一块儿空地把东西一股脑儿倒了出来。嗬,东西还真不少:有他从他的从事于远洋工作的父亲的抽屉里顺出来的形形色色单筒双筒的望远镜,有他爸帮他用硬纸板制作的简易潜望镜,还有他的私藏放大镜和万花筒。
每个人各自从中挑选了一件比较称手的工具。望远镜这东西真是不错,那是我平生头一次亲眼看到那玩意儿,虽然在当时的倍数不是很高,但也足以将相隔数十米的香瓜地轻而易举地推到眼前。由此我也深刻认识到了朱棣当年命令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重要性和前瞻性。
我们都认识李大爷,他是一个还算慈祥的老人,岁近杖朝之年。如果按照古人所说的“人生七十古来稀”来算的话,李大爷也算得上是高寿了,如果再接着两轮生肖应该有希望赶上张学良。
第二章未完,待续...